我是不是真的记得
我总感觉我记得那些事,那些永远都不会有人记起的事情。 最近总是有些奇怪的梦,梦中总会有一些人遭遇不测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,我也明白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,但心情还是有些沉重。 我会想为什么他们,为什么是这些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?我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呢?我怕会失去什么吗? 我总感觉自己可以独自过完剩下的日子,我想如果没有人要跟我讲话,我就会沉默至死。我感到讲话太累了,人与人之间似乎从来不能真正的沟通。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有时候太复杂,我真是处理不了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很难处理。我快累死了。 我倒真希望自己的生活是独角戏,我喜欢自言自语,有些话只能对自己说,有些事情真的只能自己承担。虽然我也偶尔欺骗自己说,这些事情真的会被时间冲淡,可我何时真正相信过呢? 我把自己身边的朋友都踢掉了,或许这太残忍了。是啊,我也觉得自己太狠心了。但我记得我以前经常说不要跟我走得太近。这一天真的来了。我也没有料到是这个时候啊。 我不想再跟谁讲我自己了,永远,至少我希望是永远。 都这么多年了,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能够幸存下去,或者我该说是我们这些人吧。 我欠的债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啊。 扁舟东海逝,江海度余生。 Ops, nothing related to this post. Buy yourself a lottery
让黑夜把我吞噬
那高傲的对着大地的 星星灯火 是一个永恒的谜语 抛弃我 让孤独把握吞噬 不要开口 不要打扰这片喧嚣 我是孤独的月 漫长的孤独只为了那一瞬 不要哭泣 不要扰乱这片寂静 我要沉默 我要在沉默中灭亡 谁都不要告诉我 那迷底在那里 长程相关: 三千年的往事 这个世界没有门 你们 落凡尘
物理问题的超级杀手:Hans Bethe的一生及其科学生涯
这篇文章是对由世界科学出版社(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)2006年出版的传记《 Hans Bethe And His Physics》一书的评论,此书由Gerald E. Brown和Chang-Hwan Lee编辑。 大概是在二十年前,我在冬天的时候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。我异常兴奋地走出加州理工(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)的West Bridge,准备提交刚刚通过的论文并注册博士学位。当我昂首阔步地走过校园中心高大的水泥拱门的时候,我注意到一位体格魁梧的男子正在喷泉的另一侧缓缓走动,他注视着池中的泉水,在思考着什么。我想过去和他聊几句,顺便告诉他我刚才已经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了,但是话到了喉咙口却还是把它咽下去了,我静静地站在一边。即使是在我满怀兴奋的时候,我也清醒地知道,最好不要在Hans Bethe思考的时候打扰他。我花了六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没有多大深度但是勉强可以通过的论文,但是Bethe一个下午的思考却可以改变整个物理学。 这种对Bethe和他工作的敬畏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中普遍存在,而所有为《Hans Bethe and His Physics》投稿的作者们当然也不例外。Freeman Dyson称他为“二十世纪超级的问题解决者”,普林斯顿的John Bahcall说Bethe的工作看起来是由几个人合作完成的,只是在署名的时候写的是同一个名字。在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生中,他的工作产量几乎是无可匹敌的——早在1924年Bethe十八岁的时候他就发表了第一篇,这是和他的父亲合作完成的;而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则是由他的合作者在他于2005年三月份去世后六个月提交到预印本服务器的。在这段时间中,Bethe于196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,这主要是由于他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解释了恒星中的产能机制(Energy-Production Mechanism);他提出了Bethe方案(Bethe Ansatz),这一方案在物理和数学中有广泛的应用;他于1936年至1937年为《现代物理学评论》(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)写的三篇长文被人们称为“Bethe圣经”,据说这三篇文章中不仅包括了其他人知道的关于核物理的所有内容,而且还有很多人们不清楚的东西;还有很多现在很重要的计算核质量的公式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 Bethe于1947年计算了兰姆移位(Lamb Shift),这个例子可能最能显示Bethe解决物理问题的方式:单刀直入。在战后的第一次长岛(Long Island)会议上,Willis Lamb声称对氢原子精细结构(Fine Structure)的测量和流行的狄拉克(Paul Dirac)电动力学理论不符。当时很多物理学大家,包括泰斗级的玻尔(Niels Bohr)以及奥本海默(Robert Oppenheimer),将这个现象视为物理学的一个重大危机,预示着理论的发展需要新的革命性突破。在离开长岛回去的火车上,Bethe考虑了这个问题,成功地得到了和实验观测相符合的兰姆移位值,而火车还没有走完这次长度仅为75公里的旅途。Bethe的计算并没有带来什么物理学的新革命,仅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得到了和实验结果相符的数值。这就是Bethe的风格,就像他说的那样:“学习数学是为了以备万一,但是对于具体的物理问题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足够了”以及“如果必要的话不妨大胆猜测”。所有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近似的,因此物理学中的高手们常常知道怎样避重就轻,而Bethe就是个中高手。他对于兰姆移位的计算使得其他人都相信,刚刚起步的量子电动力学(QED: Quantum…
今夜请把我忘记
又一个平安夜,月亮安详的浮在夜之海上,它似乎在享受着虚无。地面是一片荒漠,没有丝毫的生机。可月光还是静静的飘了下来,静静地落在地上。 我躺在沙砾中,任凭月光压在身上…… 长程相关: 科幻一篇-Bridesicle 晓风残月 结局篇 奈何桥 怀旧的四月 云图:脸盲症的福音
落叶
这是一场预谋。 我不知道他是谁,但我们上了一条船。 这绝对是一条船,一条快艇。否则我怎么会看到星星呢?天上有三颗星,一颗在东边,一颗在西边,还有一颗在北边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哪是东西、哪是南北,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。我感到一片迷茫。如此充实的大海仿佛只有一片空虚,这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伟大。空虚是伟大的,因为我们无法理解空虚之中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看到的知识最充实最伟大的心灵中的虚空。这颗心灵因为大而显得博大,因博大而显得空虚。但只有我们这些旁观者才明白。 空虚并非一切,因为还有一条船,两个人。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。 我感到他在笑,在嘲笑。好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什么都是好笑的。他可以在心底蔑视一切。他对这种际遇感到好笑。他觉得感应到自己的伟大是最伟大的地方。 我感觉得到这一切。 我不是上帝,但我无法知道他是不是。船舷在颤抖,我知道这绝不是畏惧。他希望摆脱我们,他希望摆脱我们,它希望粉身碎骨。承载的这两个生命太轻了,这根本无法满足它的自尊。然而,它的不幸是:海上风平浪静。 船在向某个方向飘动。我们俩谁也没有把舵。我知道在海平面上的任何方向都是错误的。他还是在笑,这让我无法忍受。现在我可以判断他应该就是上帝,因为他把对一切包括自己的冷漠放在心灵的最高处,并且能用这种笑来掩饰内心一切的善良与罪恶。 船会被毁灭的,我也会消失,唯有上帝不会。我感到愤怒不公,北边的那颗星似乎跑到了南边。我抓起了桨,把他打下了船。之后传来的是一阵轻微的呼吸声,还有那静静的笑声。 天上飘来了三片树叶,一片落在了我手中,另两片落在了海中。 Ops, nothing related to this post. Buy yourself a lottery
今夜有感
突然好想哭,想用泪水冲淡无法阻拦的情感。我一步一步踏出的脚印,已注满泪水。然后当我有一次踏步走过,泪水一点一点浸入我伤痕累累的脚,慢慢变成热泪,有一次洒在地上,流遍我们的青春祭文。日出日落,岁岁年年,泪水干了,留下了极度浓缩的盐,填补着我们美丽的祭文。 长程相关: 重读Randy Pausch Protected: 最后的晚餐? Bang! 一周总结[2011-07-18][非物理部分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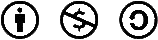
最近评论